钓鱼人不是没钓到过大鱼,只是跑掉的永远是最大的……
|
我从小就对鱼,尤其对大鱼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亲切感,追溯起来,我最早的记忆就是一条大鱼。 那是1972年,我四周岁那年的春节,爷爷起早买回一条大鱼,我清晰地记得那条鱼的模样,但当时并不认识它的品种,后来我才确定,那是一条胖头鱼,一条比四岁的我还高的大鱼。
看着那条冻得硬邦邦的大鱼,我打心底喜欢。 在我的要求下,大鱼以头朝下的姿势被爷爷吊在厨房里,我整个上午就蹲在它跟前静静地端详它,还不时抱抱它,和它比一比身高,直到大鱼慢慢开化,爷爷把它放进仓房里重新冻上,我才恋恋不舍地离开。 从那天起,我每天都要去冰冷的仓房中看那条鱼,如果没人叫我,我能围着它守上一天。 后来,那条鱼被吃掉了,没人吃的鱼鳔被我保留下来。 那是一个1尺半长,比香瓜还粗的鱼鳔。我把它挂在房子外面的高处,向所有我认识的——不论是大人还是小朋友显摆:“看,我有个大鱼鳔,比你家的鱼还大!” 一个月后,鱼鳔风干、腐败了,被我埋在菜园子里,关于那条大鱼的所有痕迹由此彻底消失。
男孩的大鱼梦 后来,不知出于什么样的心理,我每晚睡前都要在被窝里缠着爷爷,一遍又一遍地问:那条鱼有多重多高(长)、有没有一百岁、很多年过后能不能成精…… 尽管爷爷给我的答案我早已知晓,可我依然一次又一次地认真询问,反复听着重复的答案也不失望。直到有一天,爷爷给我讲了另一个故事。 爷爷年轻的时候卖粮食,赶上冬天辽河封冻时,冰面就成了过河的捷径,卖掉粮食后的空载车也都走辽河。 为了防滑,有人用高粱秆、玉米秆在冰面上铺出一条路来。 一年开春的时候,一个车把式想赶着马车继续走这里,可是到了河边,他犹豫了,毕竟已经开春了,河边的积雪已经化出一些个小水洼,冰层的承重能力令人担忧。 正在举棋不定的时候,他远远看到那条由高粱秆铺就的“临时马路”剧烈抖动起来,随后轰隆一声巨响,数捆高粱秆连带着大块儿的浮冰一齐飞上半空,冰面上顿时出现一个方圆数丈的窟窿,紧接着一条硕大无比的黑色脊背一闪而逝。 当冰块、高粱秆下落的时候,冰面开始陆续炸裂,发出声声巨响。开江了。 那车把式看得目瞪口呆,惊悸之余他马上回过味来:这是“鱼王”在给他示警,冰面已经不能再有车辆通过了!如果没有这条鱼王,他很可能葬身河中。
大家伙出水在即 接着,爷爷又讲了些什么,我记不住了。 凭着我的一贯思维,我应该探究一下这条鱼是不是有汽车那么长,是不是已经活了一千年才对。 但是,当时我想到的却不是这些。 儿时的我的词汇储备还极为匮乏,我无法充分表达对这条善良的“鱼王”的感想,于是只说:“这个鱼王……真太好了。” 现在看来,这完全就是民间故事,但当时我笃信那是真的。 在那年夏天,我开始钓鱼了,同时正式踏上了我的寻钓大鱼之路。 在16岁之前,我是没钓过大鱼的,我的垂钓轨迹仅限于老家附近的那几个小水库。 我记得读小学的时候,我钓到过三四两重的鲫鱼和半斤左右的小鲤鱼,读初中的时候钓到过1斤多重的小鲤鱼,这在当年可是我的纪录鱼,至今我仍清晰地记得它上钩时爆发出的巨大拉力,回想起来依然激动不已。
早年的底钩 18岁之后,我第一次看到了真正意义上的水库,尽管属于小型水库,但也足够颠覆我对水库的认知,原来老家的那几座小水库只能算作水泡子。这里面真的有我理想中的大鱼。 再后来,我玩得倒是挺疯,可是心心念念的大鱼却并未出现,倒是在工作后认识了几个钓鱼人,从他们嘴里又听到一些关于大鱼的故事,这些故事不是民间传说,它们都是真正发生过的。
|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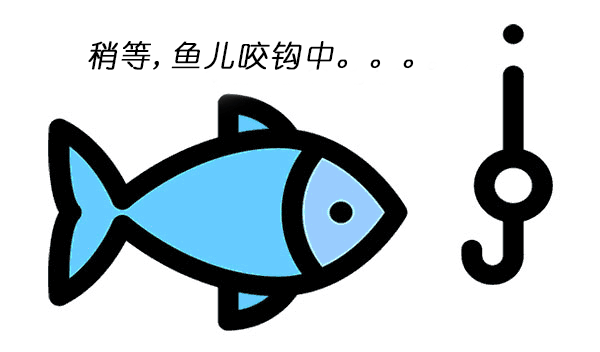





 微信收款码
微信收款码 支付宝收款码
支付宝收款码